|
周公解梦钱 http://365jiemeng.com 1990年,无论是在朱同志的奋斗史上,还是在国家历史上,都是不平凡的一年。这一年的1月27日,大年初一,朱同志给来上海过年的邓公拜年。 朱同志把浦东机场的平面图和方案给邓公看。邓公说:搞就搞新的,改造旧的意思不大。邓公笑着抬头看着朱同志,眼里有藏不住的赞赏。 邓公有一个“大工程”,需要一个关键人物来推进,朱同志正是这个关键人。现在他想给朱同志一个动力,把这个大工程启动起来。 “不用怕,报嘛!” 这个明面上的大项目是浦东开发,也是上海发展的关键,如果再不启动就要落后广东和福建了。而且,它的意义远远不止如此。 1990年(上)和2020年的浦东(图片来源:上海市外事办公室) 在来邓公这里之前,朱同志对推动浦东发展没有信心。这件事已经说了两年了,实际上很难推进。 他不是害怕做不好,而是害怕把项目向北京报告了不批准。原因有点复杂,但邓公当然心里知道。 过完年后,邓公回到北京,又给朱同志推波助澜。他对政治局的领导们说: “我已经退下来了,但是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,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,你们要多关心。” 当天的下午,领导就派人来关心了,先跟朱同志讲了浦东改革开放要注意的一些问题,等于是提个醒儿,然后问朱同志要具体的方案报告。 朱同志对领导回复如下: 上海的报告已经讨论了几个月,总是不太满意,要催的话,今天晚上就可以加班弄好。 一夜之间,报告就递交上去了。 背靠这个“大工程”,朱同志的前途完全不同,不到三年就升了三级,从一方领导,走到了国家的“宰相”。 低调、忠诚的朱同志 新同志在提拔之前,要久经群众考验才行,而最重要的是忠诚。 1987年底朱同志被派往上海时,岗位是副书记,刚刚被选为110名里的中央候补委员之一。 排名91。在被调到上海之前,他是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一名副主任。他没有得到多少选票,可能是因为他在其他地方不出名,也没有人想到他能发展得这么快。 这届在上海工作的同班同学有5位,都是副手,朱同志是其中之一。在北京的领导人眼里,他可能是一个培养对象,但他一点也不显山漏水。五人中有三人后来成为核心领导,自1988年他们在上海齐聚以来,邓公已经连续七次前往上海过春节。 他很关心这几个后备干部。前面曾在老家四川工作过,又担任一把手的胡同志和赵同志,都先后出了问题。 这时江同志已经到北京去了,陆续移交了上海的工作,开始承担更重要的职务。现在还缺一个,邓公帮江同志选搭档。如果用过去的经验作为指导的话,这次考验最重要的是忠诚。看了朱同志的简历,真的挺委屈的。 1957年大鸣大放,朱同志当时是国家计委领导的秘书,按照当时的规矩,身边的人要时常给领导提意见、搞批判。 朱同志只好上台讲了三分钟,当时大家都觉得他讲得不错,没想到过了几个月,这位老实提意见的秘书,摇身一变成了右派。 被开除党籍20年。 第2年在上海,朱同志在竞选市长时旧事重提,向全市几百位人大代表坦白自己的想法: 我是一个孤儿,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……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……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,我也不计较。 没见过父亲样子。12岁的时候目睹母亲病逝。和叔叔一起在湖南长沙长大。在上海考上清华,刚参加工作就当了科室副主任,然后被冤枉了20年。 前十年在国家计委机关教老干部数理化,后十年在五七干校种小麦、棉花、水稻。他还放牧牛、羊和猪。还做过炊事员。不知道做饭好不好吃。 1978年被老领导马洪捞上来之前,朱同志刚刚花了两年时间和一群徒弟爬电线杆搞电力。从拉电线开始,手把手教他们安装22万伏特的电线和11万伏特的变电站。 那一年他50岁了,还在狂热地工作,但“一事无成”。像朱同志这样的人生经历,是常人难以想象的,忠诚这个词是那么沉重,那么难以理解。在看这些材料的时候,小编确实想到了一个现在很流行的词。 “长期主义”。 人的一生太短,也很渺小,即使朱同志有这样的才能,也会被大势所左右,浪费了他的半生。 还好,老领导晋升回到国家计委、经委工作,“传奇伯乐”宋平慧眼识才,把朱同志列入高级后备干部名单上,东山再起,达到人生巅峰。 就拿普通人来说,即使有才华,50岁以后人生也完了,还没怎么起就落落落落……里面一点波浪都没有。 如果你想完成一件事,你只能依靠长期的坚持,慢慢“熨平”不可控的时间周期,忠于工作和生活,忠于事业和目标。即使等不到大势,有了出路和机会,你也可以赚一份温饱,心满意足。 经历了人生“三起三落”的邓公比朱同志看得更深、看得更远。中国的历史周期波动了数千年,有起伏的周期,大多是大混乱和大治理之间的过渡,起伏的幅度大多是史诗级的。根据历史经验,过去几十年的改革不可能不出现政治乃至社会的混乱。一乱一治代价太大,邓公只好把稳定放在首位,把改革的波折压到最小。因此,忠诚的底线无法被穿透。一个戈尔巴乔夫就足以摧毁一个大国。 已经快60岁的朱同志,在等待了半生之后,终于有机会把自己的长期坚持,嵌入到历史的大势之中,靠的是这份忠诚和“长远主义”。 造到一半的东方明珠 坚硬、真诚的朱同志 光有忠诚是不够的,还得有能力。那个时候,所有的保守派都在大声呼喊忠诚,以至于他们什么事也做不成。朱同志的脾气是出了名的,人们对他的评价有赞扬和批评,朱同志不太计较得失,在任职期间会留下“自己的棺材”。能做的事,大半尝尽人间滋味。 事比人大。 上海“卧虎藏龙”自古以来就交织在一起,外地人的干部要想立足就需要一些手段。 朱镕基同志12月抵达上海,第二年4月正式就任上海市长。在保持低调的几个月里,他被当地同志找麻烦。有人在简报里挑明:还没来上海就说想当市长,是不是不谦虚、不够谨慎? 确实有这个事,当时朱同志接受记者采访,除了坦诚,也缺乏经验,记者的问题大概是你当了副手后有什么打算?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。答案也是例行的行,表现出决心啊,对工作有期待,要为上海多做贡献,语言组织的好,也是可以出彩的。朱同志直言不讳的说:“中央派我来当市长,而不是副市长,” 如果涉及选举规则的严肃性,还是要向人大代表解释清楚。话刚说完,高情商的江同志就站在他身边,给他打圆场: “举行记者招待会是以中央提名的市长候选人名义,所以我认为朱同志讲这句话从原则上讲没有错。” 实际上,这事儿朱同志事先跟领导汇报过了,领导明确可以说,算是表达支持吧。 性格不同,朱同志的选择也不同,作风既硬又诚恳。核心永远是对这件事,怎么做事情怎么来,密切关注它,做不好批评自然是必不可少的。 他严厉地批评同志,更严厉地批评自己。刚上任时,朱同志就说自己基层工作经验不丰富,“以后可能会在这方面犯错误”。在上海工作三年多,朱同志开了了三次民主生活会,每次提到自己的工作作风,说的不止一次毫不留情,有兴趣的可以找他的演讲看看。 表里如一是朱同志对带队伍的定义,也是对“谦虚”的定义。在公开场合,朱同志对江同志很尊重,他们的关系非常融洽,当了总理后也是如此。 1999年,他访问了美国,并与克林顿举行了记者招待会。他对美国总统和记者们说:“我自己不想来。江同志要我来,我得听他的。 “上海要发展金融主业,这是朱同志的思想和目标,却刻意解释不用提“中心”。大肆宣扬是带感,也容易树大招风,难以成事。事情做得好,自然是老大,谁也不敢轻视,总是挂在嘴上吹牛,牛不到哪里去。 细琢磨琢磨,所谓傲慢、谦虚、狭隘的风格,其实都很难相处。它们的本质是一致的,人大过事儿,太过关注自己的感受和形象。 还有表面上谦虚忍让、包容提携、甚至与世无争,转头就要算计小鞋儿的尺寸,更让人头疼。 朱同志和这样高层作风的人相处,会很淡定,领导也放心,下属也不用担心被算计,事儿办得好还会被快速提拔。 要了解朱同志的“无我”状态,请看下图。夏天在上海的一条街上,当水管爆裂时,他跑到现场,紧握双手盯着大坑,别人的注意力也就没法游离了。 预判领导的预判 朱同志在上海任职期间,邓公来过四次。不知道他拜过几次年,但邓公对他的印象一次比一次深。据龙安志《朱镕基传》记载,1990年,朱同志拜年汇报工作时,邓公就发现,朱同志不会提前准备讲稿,但讲话清晰成熟,细枝末节的数字一开口就出现在他的眼前。 这是一种掌控全局的气场。从此以后,提到朱同志,邓公就说三个字: 懂经济。 邓公在看朱同志,朱同志也在观察邓公。1990年,朱同志连夜提交了浦东发展规划,显然已经做好了准备。但他未必完全确定领导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,邓对他的回应毫不含糊,对两人来说都很成熟。 另一个重要事件是1991年关于姓“资”还是“社”的争论,有个未必众所周知的起点,也是朱同志。 这一年邓公又来到上海过春节,朱同志陪同他在上海参观考察,两人的讨论也越来越深入,邓公说: “不要以为,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,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,不是那么回事,两者都是手段,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。” 朱同志明白了,拿起笔记本记了下来。 回来后,他亲自带着同志们整理了邓所说的话。 当时的《解放日报》总编辑周瑞金在与该市宣传干部一起工作时,“碰巧”听到了这个故事,抄下了他们的小笔记本。 所以后面有一篇署名为“皇甫平”的文章。根据周瑞金口述的历史,这些文章在发送时,上海团队成员对内容没有异议,只是对未能按程序及时提交提出了一些意见。 这些文章引起了极大的骚动。北京TopLevel的党报社长以个人身份来上海兴师问罪。搞改革怎么能不分姓资姓社呢?让周瑞金写报告向上级解释。 周没有理睬他的请求: (我感到很可笑)难道不知道我们连续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四篇评论,会毫无根据吗?我能够随便按照个人的意见来写吗? 这年3月,朱同志调到北京工作,但他远不是保守派的对手。不仅朱同志,比他先来北京的伙伴江同志,都面临着很大的困难。 江同志在1991年7月1日的讲话中强调,既要防止和平演变,又要坚持改革开放。到了公开播发的新闻里,预防和平演变是众所周知的,但改革开放却很少被提及。 江同志很不高兴,要求上述报纸再发表一篇强调改革开放的社论。这位社长却在头一天中央台《新闻联播》,先期播发的文章摘要里,刻意加了句: “要进一步改革开放,就要问姓社姓资。” 江同志也较劲了,看完《新闻联播》马上打电话给上级,要求立即修改,删除这段多余的文字。 在中国新闻史上,一篇由顶级报纸发表的文章,第二天会以不同的版本发表,这也是独一无二的。 两个月后,江同志公开批评报纸海外版在另一次讲话中强调了“防止和平演变”,而忽略了其他讲话内容。 江同志当众讲话都有这样的困难。朱同志做事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。关键时刻还是邓公出马,他选择的两个合作伙伴配合默契,还给他们加油,并送了一程。 1992年,他改变了行程,在春节前到广东“南巡”,重复了一年前在上海对朱同志说的话。 回到上海后,朱同志不在,邓公在他任内推动修建的、通往浦东的南浦大桥上,快乐地拍了一张自己的照片。 同年10月,朱同志从候补委员晋升为常委,连升三级,成为核心管理人员。 真正的大工程,改革开放的战车,已经在轰鸣中启动。 参考资料: 一场“姓社与姓资”的交锋(周瑞金口述),上海文史馆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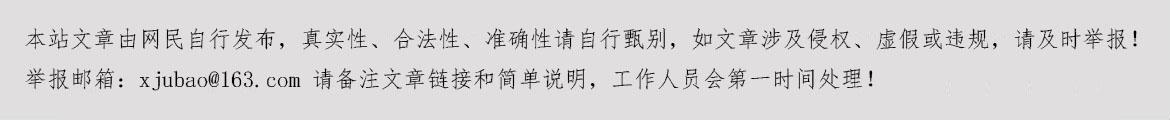
|
 鲜花 |
 握手 |
 雷人 |
 路过 |
 鸡蛋 |
分享
邀请